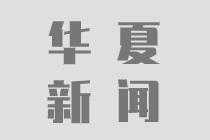《隐秘的角落》没能把对恶的淋漓揭示导向善的萌发
◆《隐秘的角落》剧照
《隐秘的角落》可谓是今年国产爆款网剧的肇始之作,连带着剧中台词“去爬山”和配乐《小白船》都在大众话语中拥有了别样的意涵。细数《隐秘的角落》大受欢迎的原因,大概是作为一部网剧,难得地呈现了较强的艺术风格,不仅打破了一般的悬疑推理剧的套路,一开始就把罪犯呈现在观众面前,而且剧中从大到小的一众演员,俱演技在线;导演的影像语言也颇为娴熟。
然而,一边倒的对该剧的赞颂,却也让人感到不安。此不安来自电视剧所呈现的灰暗——并不是来自电视剧的镜头语言和光影所制造的整体氛围的灰暗,而是这种氛围所隐喻、暗示甚至夸大的那种灰暗,即人性之“恶”。由此引发的,是电视剧该如何表现恶的思考。
电视剧表现恶不是目的,它只是方式
《隐秘的角落》某种程度上是恶的集成,似乎是所有被侮辱被损害以致带着各种创伤生活的各式人物的汇总。冷血而杀人的凶手、出轨而冷漠的妻子、内心阴暗的小孩、歇斯底里的母亲……与底层的生活样态的加持,构成了一幅残酷物语般的图景,生活的血淋、人生的悲苦,正面和解救力量的孱弱与无力被极致夸大,让整个电视剧直到最后只剩下难以言说的无奈和冰冷,于是只能遗留冷漠、叹息与脊背发凉却难有反思,也看不到任何希望,这或者是这部剧给人最大的冲击之一,但也是这部剧最大的问题之一。
电视剧是不是该表现恶呢?毫无疑问,犹如月亮背面,恶是生活的一部分,其数目又是无限的,自然且必然被电视剧所呈现和反映。正像雨果说的,“我们必须容纳一种关于我们世界和我们自身中存在恶的看法,不论那个恶多么触犯我们的自恋”。所以,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在电视剧中表现恶,而是怎么表现恶,或谓之我们表现恶的目的是什么?
左丘明说 “善不可失,恶不可长”,因而要“惩恶而劝善”。这也是深植在中国人文化基因中最具共同认知的价值观之一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电视剧表现恶不是目的,它只是方式。如果一部电视剧只是为了表现恶而表现恶,那么它的影视语言越是新颖、叙事越是巧妙、表演越是精湛,它于社会与人的意义就越是要被打上一个问号。因为,电视剧是当今影响力最大、受众面最广的一种文艺样式和文化产品,它对社会环境和大众认知所起到的作用,决定了它的社会责任和义务。通过 “恶”之途径达“善”之目标,既符合观众心理期待,也是其文化功能的体现。如果一部电视剧的播出最后让人感慨“人间不值得”甚至细思恐极,很难称这种创作是成功;而一部电视剧在对恶的淋漓揭示之后,没有让人反思恶,没有让善得以萌发,那么则很难说是有意义和价值的。
一味呈现纯粹的恶,让电视剧的思想性大打折扣
罗曼·罗兰说“善与恶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”,善恶之间的争斗是电视剧的母题。近年来,社会的发展、媒体环境的开放,以及人们对于生活世界各个层面在文化精神上探求的加深,都使得以探索和展示恶为主题的电视剧越来越多。然而如何有意义地表现恶,突破原有的窠臼,让人反思恶,从而达到向善的效果,则值得深思。如果我们将电视剧对于恶的表现的目的进行更细的分解的话,概而要之,可将其分为三个层次。
种种我们并不曾在意的问题有可能是人性之恶的根源,而恶本身可能也是复杂且充满着矛盾性的,表现这些揭示这些,应该是电视剧表现恶的第一层追求。一直拥有很高收视率的海外剧《双面法医》就向我们展示了善恶的复杂和矛盾:主人公德克斯特在白天是警察局一名普通的法医,从事血迹图案分析工作,协助警察破案;而到了夜晚,他则化身为一个杀手,专门猎杀那些做了坏事却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而逃脱法律制裁的人。电视剧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英雄,而是揭示其捕杀这些坏人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舒缓自己的杀戮欲望,但又难以说他纯粹是一个恶人,因为那些被杀的,也确实恶事做尽。到底该如何认知他和他的行为?电视剧就在这种矛盾困境之中让观众进行评判、反思和争论,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善与恶的边界。
而更高级的表现是揭示这些恶背后所勾连的各种因由,深挖这些因由对“恶”所应负有的责任。比如韩剧《大叔》中女主的犯罪是因为有黑帮势力的胁迫,而她因为没有任何的地位和依仗,只能被迫违心做事。正在热播的韩剧《恶之花》中,男主及其姐姐所作的恶,很大程度上是乡村愚民对于其父所犯的罪过迁怒到儿女身上,以及对于男主所患的精神疾病的愚昧无知所造成的。这些电视剧在呈现、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上,把恶背后所纠缠的问题引入哲理深思之中,不是简单地只表现恶,而是表现恶的多重面相或矛盾之处或恶背后所牵连的各种问题,从而让人增加对于人性和善恶的反思批判。